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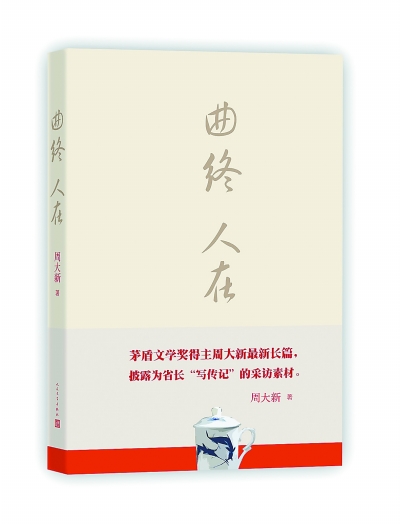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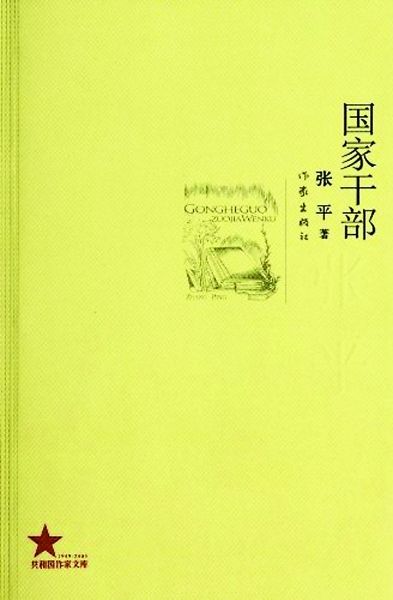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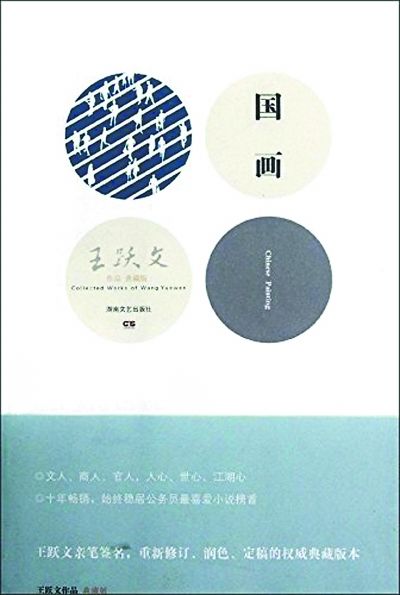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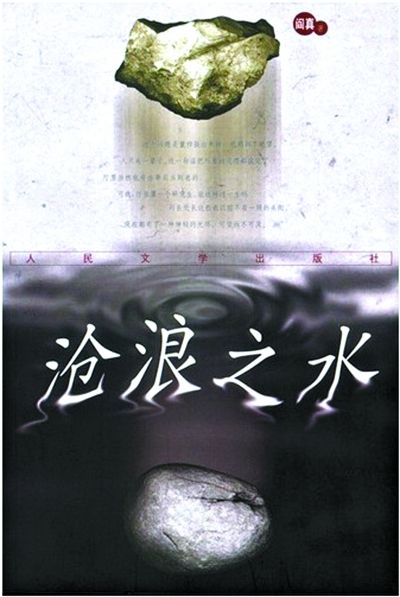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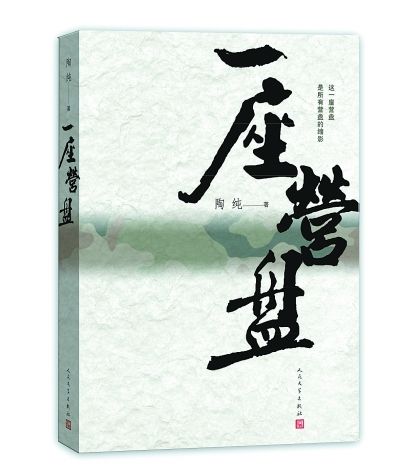
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被《一座营盘》震撼了,“这是军队反腐题材文学的开山之作。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、级别之高、问题之大,都是前所未有的。”在他看来,《一座营盘》是突破军队反腐领域雷区的一部力作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反腐题材创作曾一度兴盛,但前几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近期,随着《一座营盘》《曲终人在》等新书的出版,反腐题材再度进入读者视野。这背后有突破,也有困惑与无奈。
1“大老虎”落马带来写作勇气
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的历史上,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的问世是个例外。
去年7月,《中国作家》文学版编辑佟鑫听说作家陶纯正在创作一部军队反腐题材小说,就密切关注起小说的进展。她说,这部小说如果不马上抓到手里,担心很快会被“抢”走。好在今年1月,佟鑫终于等来了小说的完稿,杂志社为此还破了老规矩,“我们的出版周期一般很长,来稿至少要等两三个月才能采用,《一座营盘》不到20天就登出来了。”佟鑫介绍说,这部30万字的小说分两期刊登在《中国作家》2015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。
“《一座营盘》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,肯定发表不出来。”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陶纯心里很清楚,十八大之前,军中腐败是公认的雷区,肯定是不敢这样写的。促使他下决心写《一座营盘》,有一个重要的契机——十八大以后,风向变了,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腐,“在我党历史上,像这么大规模的、坚决的反腐,从未有过。所以这本书与党中央大力反腐、军中‘大老虎’纷纷落马有直接关系。”
“说实话,我早就想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军营为蓝本写一部长篇小说,但写三十多年军队的变革,如果不涉及军中腐败,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,我认为那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。”陶纯说,他其实一直在等待,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写出来,“终于我等来了,我是幸运的。”
和《一座营盘》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军旅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新作《曲终人在》,该作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中国官场的纵贯线,也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,官场和官员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,直击腐败问题。
这当然不是巧合,军中“大老虎”的纷纷落马,为两位军旅作家带来了写作灵感,更给他们带来了写作勇气。
周大新明确地说,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落马,直接催生了《曲终人在》的写作。“我们过去都在总后大院住着,大家也都认识,没想到他贪污那么多,光是酒他就收了1500箱。这的确让我很吃惊,这件事刺激了我。”周大新说,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了高官们,但他们光为个人、家族的事情操心、忙乎,“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写了这部书。”
两位作家甚至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呈现了谷俊山的文学形象。《一座营盘》中二号人物孟广俊便是以谷俊山为原型创作的。在接待、酒宴、招标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中,作家勾勒出这个军中“老虎”几十年的人生历程,孟广俊一路春风得意,曾经志得意满地感觉“自己就是一九四九年打进南京总统府、扯下青天白日旗的英雄”。而老干部们也由衷感叹道:“小孟这个人,若生在宋朝,他就是宋江;若生在唐朝,他就是秦琼。”
在《曲终人在》中,同样也有谷俊山的影子,“我写的人物都是虚构的,没有一个是真的,但有些事情是真的。”周大新介绍,书中的人物魏长山家里地下室放了很多酒,还盖将军府,“那是谷俊山的做法。”
“社会的热点往往就是作家的关注点,当下国家大力反腐,中国作家应该会有人在这个题材上一展身手。”陶纯预判,反腐题材创作这几年还可能出现更多,“反腐永远在路上,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,也关系到你我的命运,为什么不用手中的笔,以笔作刀,来参加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?”军人陶纯就像冲锋在前的战士一样,发出了豪言。
2又登上多年前上过的“贼船”
在小说《酒国》中,莫言对20世纪90年代的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进行过深刻批判。他近来也说过,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。
事实上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张平、王跃文、陆天明、周梅森等作家,都涉足过反腐题材的创作,但这些年,他们渐渐淡出了,人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还都是这些作家昔日作品的不断重印,鲜见同类题材新作。但最新消息得知,陆天明、周梅森将重出江湖,再度进行反腐题材的创作。
“我是下决心要再搞的。”老作家陆天明说,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,他有作家朋友也在蠢蠢欲动,想进行反腐题材创作,而他自己已接到数家公司的剧本和小说的创作邀约。
陆天明坦言,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,反腐题材出了很多,今天再写,怎么写,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——当下的反腐,都有了深入发展。“腐败官员做的事,当年我们再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,这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家伙胆子咋就那么大?”陆天明还提到,反腐手段、反腐形式以及反腐斗士自身的形象也有了新变化,只凭道听途说的二手三手材料无论怎样也难写好。
周梅森写过《至高利益》《人间正道》《绝对权力》《国家公诉》等反腐小说,这些年似乎隐退了,一直悄无声息。但他透露说,目前正在进行40集反腐电视剧《以人民的名义》的剧本创作,并有写成小说的打算,目前已进行到一半,周梅森笑称,“我又上了‘贼船’。”
周梅森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愿意再碰反腐题材了,他和陆天明的想法一样,“公布出来的腐败案件的广度、深度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,生活远远走到作家艺术想象的前面去了。”他反复问自己,“是能提供更有意义的故事呢,还是能提供更有意义的人物形象,或是更有意义的思想启迪?我觉得很难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。”这个念头最初牢牢操控着他,他几次拒绝了创作邀约。
直到去最高人民检察院体验了生活并查阅了贪腐案件材料,甚至和落马官员有过深入接触后,周梅森才改变了想法,“我发现,这个题材依然能做。”
周梅森找到了突破口,这部《以人民的名义》选取的故事,正是来自公众广为熟悉的案件:从国家某部委干部的家里搜出了两亿三千多万元,通过这次搜查,一个官员人性深处的黑暗像剥洋葱一般被层层剥开,作家由此拉开了某省的一场政治大地震和反腐大较量的序幕。“尽管开局的这个小官巨贪案件举世闻名,但作家需要做的是往人性深处、心灵深处挖掘。”周梅森说。
周梅森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,同样给他提供了素材。周梅森久居南京,他对江苏一些落马官员很熟悉,他觉得很多人对落马官员有一个误解,觉得他们天生就是大坏蛋,党组织当初重用这些人真是瞎了眼。“通过我和他们的接触来看,他们其实人都很能干,有开拓精神,但他们灵魂上往往又都很孤独。”周梅森分析说,有的是因为心里不平衡,看到企业家那么有钱,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拥有?有的则是因为深深的孤独,需要找一些化解的地方,而走上了腐败之路。“这是我的新发现,有了这些新发现,就可以进行创作,如果找不到超越新闻报道的东西,那就不能进行创作。”周梅森说。
3作家“踩着钢丝”进行创作
“在写作过程中,我的内心总是很挣扎,就怕出问题。”周大新坦言,中国作家大都不愿意写这类小说,一方面是不想介入政治太深,另一方面,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好表现,以及还有很多无形中的约束。《曲终人在》就是在如此纠结的状态下写成的,即使完稿后,周大新心里依然没底儿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安慰他:“为什么不可以发?实际生活中已经抓了这么多腐败官员,难道文学不能表现吗?”《曲终人在》一书出版后,周大新非常紧张,怕有负面反应,他在一段时间内都盯着各路网站——还好,都是正面反应。
“写作过程中,我一直有一个担心,怕别人对号入座,当然不怕谷俊山这样的原型对号入座,他进去了,想打击报复也没可能了。”陶纯说,他是担心身边熟悉的人、曾经认识的人,尤其是一些领导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。“但好在我笔下的一些负面内容,在全军普遍存在,大家都心照不宣,见怪不怪。”陶纯说,最后他把碎片化的东西、星星点点的细节,捏合、塑造成另外的样子,让别人觉得不是自己。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,陶纯还有意做了一些处理,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——A基地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,下面有师、旅、团。像这样的编制,全军是没有的,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、旅、团建制。
对作家们而言,反腐小说的写作还要把握好“度”。“军营中的人和社会上的人一样,都是复杂的,很难用一个‘好’字或‘坏’字来概括。”陶纯说,至于如何把握,主要看作家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,揭露丑恶,如果是希望国家好、军队好,就能把握得准,“我的化解方法很简单:把布小朋这个一号人物写好、处理好,让他身上的浩然正气贯穿到底,这部作品就不会有大麻烦。”
“反腐小说其实不容易写好,除了题材敏感、雷区多、容易惹麻烦之外,还有一个就是它纪实色彩浓,搞不好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。”陶纯总结说,这也是很多作家为什么不想触及这个题材的原因。
周大新、陶纯的冒险写作,几乎立刻获得了业内的首肯。“大环境的改变,为反腐小说提供了叙述上的安全感,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,使这类题材开始向严肃的深度去开采和挖掘。”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如此说道。
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西元说,军队腐败问题大家不是看不到,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可是不知能不能写、怎么写,久而久之,选择性回避就成了选择性遗忘,军旅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真空。“因此,一旦有作品闯进了这个领域,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反响。《一座营盘》把这些东西从人们的记忆当中统统打捞了出来,仅此一点,就足够触目惊心。”
“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完完全全赤膊上阵,搞一部轰炸性的小说。如果是那样,还不如写报告文学,写新闻报道。”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认为,反腐题材写作,不仅仅是直面社会,更多还要指向人类的处境、人类的未来,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。“《曲终人在》就有这种非常现代的想法,以往的反腐小说是没有过的。”施战军说。
他进一步解释说,《曲终人在》中,事关一个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,从妻子开讲,儿子、姑妈、司机、保姆、前妻、继女、法师、官场同事、模特、总裁等等各有各的角度、倾向和口音,但每个讲述人在谈说“他者”之时更在诉说“自我”,合起来构成了荒诞绚烂的乱麻奇景。本应是给刚刚作古的省长立传用的材料,却成了调式不一的混声杂音,讲述人更在意的其实是自我的造像。施战军因此认为,“周大新的小说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,同时也是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,有这种艺术探索的勇气,又敢直面当下生活,这样的作家应该对他致以敬意。”
对话
写“反腐”但别限于“反腐”
受访者 文学评论家白烨
采访过程中,很多作家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小说贴上反腐小说的标签,作家王跃文就非常明确地对本报记者说:“任何类型化标签对作家和他的作品都不是赞赏而是贬损,简单的标签化定义是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消解。”
但为了表述方便,我们又不得不沿用了“反腐小说”这个标签。甚至会顺着这个“标签”的指向,回溯多年来反腐题材创作的发展、样貌,这对于观察今天和未来的创作走向,是必不可少的。于是就有了这次对话。
问:首先请您简单回顾一下反腐小说这些年来的生长脉络?
答:“反腐小说”这个说法因对一些作品只做简单的题材归类与内容指认,在文学评论中并不怎么常用,更多的时候是媒体的一种用法。好的小说,一般都是超越单一题材的,因此许多作家也对这一说法不太认同。这里,我们权且沿用这一媒体的说法。
反腐小说与现实题材写作的关系十分密切,其较早的源头可追溯到新时期之初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、柯云路的《新星》等。上世纪90年代,由河北“三驾马车”何申、谈歌、关仁山带来的“现实主义冲击波”,把反腐与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;与此同时,张平、周梅森、陆天明的小说,又把“反腐”与“官场”内在地结合起来,促进了反腐小说向官场小说的有力过渡。进入新世纪之后,官场小说有三部重要的代表作,这就是王跃文的《国画》、阎真的《沧浪之水》和李佩甫的《羊的门》。后来还有一些偏于通俗或流行于网络的官场小说,如王晓方的《驻京办主任》、老乔小树的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、黄晓阳的《二号首长》等。现在的类型小说中,就有被称之为“官场小说”的一个类别。
问:反腐小说创作总体是个什么样貌?在您看来比较不错的作品都有哪些?能否推荐几部?
答:反腐小说在其发展演进中,已逐渐超越了单纯的“反腐”,越来越走向对于官场现状的生态揭示和对于基层官场的深入透视。因此,现在常用的官场小说说法,在包含反腐小说的同时,事实上已替代了反腐小说。
我认为,从反腐小说到官场小说,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的作品,如周梅森的《绝对权力》、张平的《国家干部》、陆天明的《省委书记》、王跃文的《国画》、阎真的《沧浪之水》和李佩甫的《羊的门》等,都值得一读。近几年,还冒出来一个叫余红的文学新人,先后写作了《黑煤》《鸿运》《琥珀城》等长篇小说,也别具韵致。
问:大约5年前,反腐题材创作一度受阻,但我发现,最近这一年来创作势头开始回暖,“局长”“市长”“县长”之类的小说又开始多起来了,对此您怎么看?
答:反腐小说一度受阻,与其自身存在很大问题有一定关系。一个时期以来,这类作品较受欢迎之后,一些作品便在“反腐”的同时“渲腐”“炫腐”,不仅写得相当俗气,又相互跟风。如《黑冰》市场销路很好,便有《黑血》《黑雨》《黑风》接踵而来,使得这类作品带有相当浓厚的黑幕小说色彩。还有的一味渲染官场厚黑学、谋略术,停留在对欲望的赤裸裸展示上,甚至堪称官场升迁的“教科书”,作家该有的批判精神根本不见踪影。
现在反腐小说势头回暖,既有反腐成为社会常态的原因,更因为作品本身的质量上来了。写“反腐”不限于“反腐”,写“官场”又超越了“官场”,作品具有更丰盈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内涵。
问:从反腐小说成长史看,《曲终人在》和《一座营盘》的出现会是反腐小说的一次转折吗?
答:周大新的《曲终人在》和陶纯的《一座营盘》,确是近期让人眼睛一亮的两部长篇新作,他们确实都与“反腐”不无关系,却又远远超越了“反腐”本身。《曲终人在》里的欧阳万彤、《一座营盘》里的布小朋,都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、基地司令员高位的。但这个过程却危机四伏,充满凶险,因为环绕着他们的贿赂方式无奇不有,行贿者也此起彼伏,这些都令人防不胜防。可以说,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并与之巧妙地进行斗争,是他们最为日常也最为艰巨的任务。他们并非反腐英雄,却是拒腐的斗士,这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,要更为难得。这两个人物形象,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,有其正向的独特性,也有其艺术的典型性。涉及反腐的小说,注重正面描画人物,多维审视人性,这两部小说做了极为成功的尝试。
问:反腐小说创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,作家们处理得如何?
答: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在作品中内在地包含“反腐”,而不是局限于单向地“反腐”,深入地触及“官场”,而又有力地超越“官场”;同时在获取生活素材和塑造人物上,要有新的视野、新的胸怀、新的角度和新的手法。可以说,大多数作家在这一方面还陈陈相因,少有突破,尤其是在流行于网络的类型小说写作中,内容同质化、艺术粗放化的倾向更为严重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,周大新的《曲终人在》和陶纯的《一座营盘》这样另辟蹊径的写作,既是凤毛麟角,也显得十分重要。他们以成功的经验告诉人们,即使是涉及“反腐”,触及“官场”,也可以花样翻新,也可能自出机杼,关键在于作者对现实生活要有深入的研究与细切的体味,对时代新人要有充分的认识与独到的把握。总之,这也和别的文学写作一样,倚仗的是作家自身的修为与艺术的内功。(记者 路艳霞)
